何兆武在《冲击与反响:何兆武谈文化》中提到: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,普遍性应是第一位,特殊性是第二位。近代化是一条共同的道路,并不存在说走哪国的路,尽管各个民族有各自的特色。
他指的当然是中国近代史的各项运动,洋务运动也好,百日维新也罢,当时吵得很凶的其中之一就是到底该如何定性这项运动。这样的艰难决策同样也出现在百年后的改革开放上,亦或是更早的「姓社还是姓资」站队上。《邓小平时代》里,有几处讲述了邓小平如何处理这些敏感的定位问题:一处是对经济特区的称呼上,强调其是「经济」特区而非「政治」特区,但其实特区依然享受许多政治上的优惠政策,而这些政策也在带动经济上起到很关键的作用;另一处是改革开放的「姓资」问题,他着重强调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强调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,而非走资本主义路线,从而堵住许多保守派的嘴,让大刀阔斧的改革得以进行。
晚上读了一会儿《死屋手记》。其中,总序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出了深刻的概述,很契合我的观点:一、陀氏的小说,是思想的小说,是剖视人性的小说,故事和情节只是他借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动起来的要素而已;二、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是对话化的,通过对话将自我意识外延,与其他的人物产生联系,甚至与读者产生联系,以至于读完陀氏的小说,脑海里总会回响其人物的自白或者对话来,久久不能散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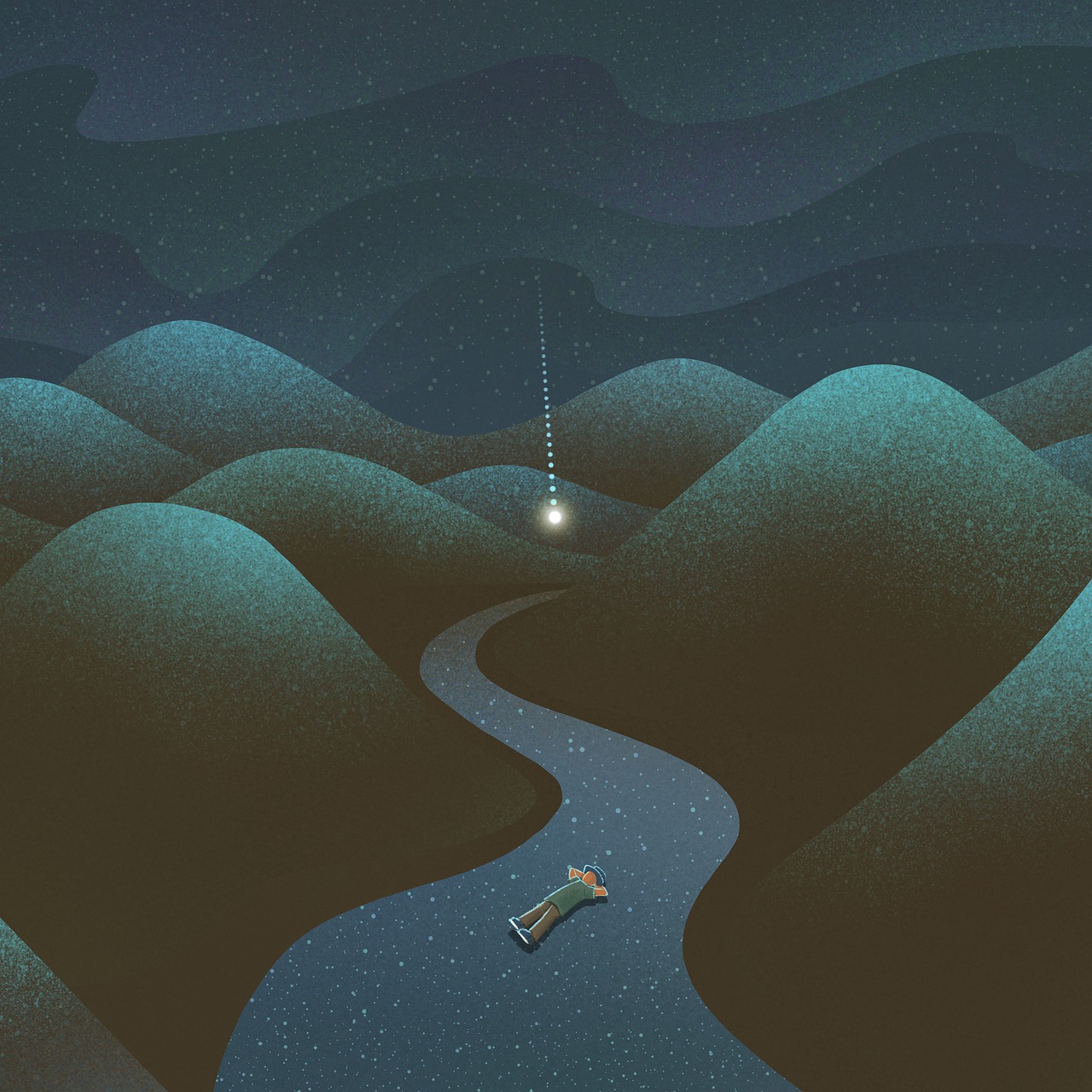 随机漫谈
随机漫谈